快訊
- 大阪市獲捐21公斤金塊 指定用於更新老舊自來水管線
- 馬尼拉華人區驚傳分屍案 凶嫌落網自稱台灣籍
- 生日當天被捕!英前王子安德魯牽扯淫魔檔案 涉公職人員行為不當
- 卸任小英去哪裡?山上都是她的「毛朋友」 拔菜也講求快、狠、準
- 尹錫悅遭判無期「能否獲特赦」引關注 支持者激憤悲哭
- 日本雙人花滑「木原運送」超吸睛!木原龍一親揭原因:不希望璃來受傷
- 歐洲五大情報首長:俄羅斯無意在今年內停戰
- 白宮帳號PO文稱Taiwan還放國旗!與中國「平起平坐」列美22大貿易國
- 發動「光之革命」擋下尹錫悅戒嚴 南韓全體國民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
- WBC台灣隊初三開工!旅日3強投今報到 徐若熙26日交流賽將登板對台灣
- 第一夫人露臉了!賴清德說馬年冷笑話 太座吐嘈:10個只有2個好笑
- 快訊/南韓前總統尹錫悅逃過死刑 內亂罪成立遭判無期徒刑
- WBC》神之左腕出動!郭泓志餵球震撼國手 同框王建民給驚喜
- 權貴菁英與派對 艾普斯坦檔案揭露跨國政經版圖
- 射程涵蓋全南韓 金正恩展示巨型多管火箭發射器
- 武廟遭嘔吐物噴濺無礙!賴清德初三台中彰化拜廟 合體何欣純送福袋
- 即將和川普簽署貿易協議 印尼砸70億美元買美國農產品
- 黃國昌擬開「晚間帶狀政論節目」突圍 柯文哲:通常叫我就會去
- 45年來最嚴重死傷!加州滑雪團遇雪崩釀9死
- 蕭美琴、蘇巧慧前進「惜食廚房」親自打便當!超暖畫面光
一頭癱倒的豬:當西方收緊動物實驗 中國加速基改大型動物打造生技優勢
2025-11-02 08:30 / 作者 李寧怡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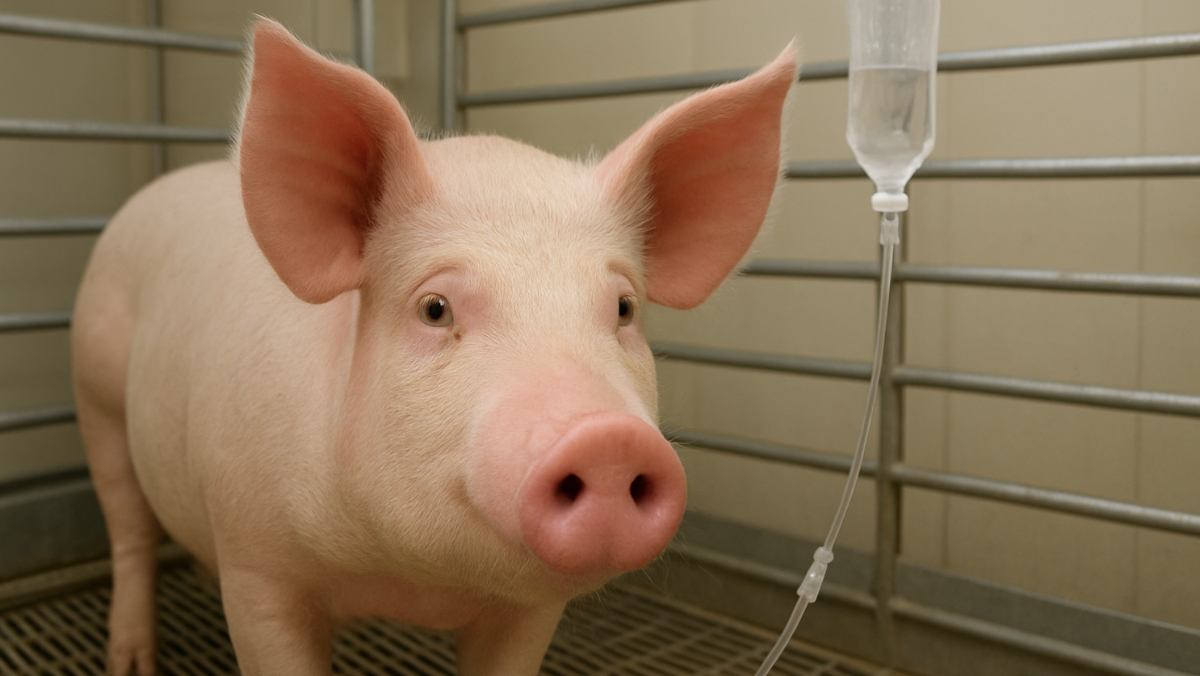
實驗豬隻示意圖。圖:AI生成
全球對動物實驗的容忍度越來越低,在西方國家,許多生化研究因動物實驗相關審查而延宕,動保團體的長年積極倡議也推動許多監管措施。此一趨勢卻成為中國的良機。中國學者為研究神經相關疾病,藉由基因工程製造出受漸凍症所苦的豬、罹患自閉症或思覺失調的猴子,均不受任何倫理限制,成為其科學發展的一大優勢。彭博新聞報導,在北京一間實驗室裡的一頭小豬才幾個月大時,四條腿就開始支撐不住。牠最初是在實驗室的水泥地上有如暈眩般搖晃,努力想站穩;幾週後,牠就徹底癱倒。等牠一歲時,已經開始呼吸急促。
對於53歲的北京清華大學神經科學家賈怡昌來說,這一幕令他難受又振奮。他研究「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」(ALS,俗稱「漸凍症」)多年,原本一直在鼠類基因中植入ALS相關基因,試圖讓小鼠罹患漸凍症,但始終未果,最後卻在豬隻身上重現這種殘酷病症。
人類若罹患漸凍症,肌肉會逐漸不受控制,最後陷入全身癱瘓,多數患者只能存活三年。
小鼠植入漸凍症基因後安然無恙、豬卻癱倒,成為賈怡昌找到的關鍵線索。他因此發現小鼠體內有一種特殊基因,藉此研發出可望減緩漸凍症病程的療法。這項名為「SNUG01」的療法,今年已獲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(FDA)批准進入人體試驗,並將其列為有助對抗罕見疾病的「孤兒藥」(orphan drug),享有稅務優惠。
賈怡昌的工作呼應了中國的國家戰略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提出,要在多個由歐美長期主導的領域成為超級強國,不僅人工智慧(AI)、軍武發展要超越對手,生物科技也是他點名的重點領域。
中國製藥業數十年來主要生產仿製藥,複製其他國家已開發的藥物。在中國政府看來,大規模投入基因編輯研究,是擺脫對外國藥廠依賴、發展自主創新藥物的關鍵。
中國為了在生技領域勝出,挑戰更多界線。針對豬、猴、犬等大型動物的基因工程,在中國限制極少;反觀美國與歐洲的監管機制均要求層層倫理審查,幾乎無法推動同類研究。
西方社會除了對動物試驗的限制日益嚴格,動保團體長年在實驗犬隻繁殖場外抗議,也迫使多間實驗室關閉,航空公司也因此停止運送實驗用猴子。在美國,民調顯示80%民眾支持逐步終止動物實驗,針對大型動物用於實驗的倫理審查制度,更讓研究進度近乎停滯。
中國對於動物實驗則監管鬆散,主要針對動物來源合法性、檢疫與生物安全,動物承受痛苦等倫理問題大多不在考量之列,倡議動物權利的聲音常被斥為「輸入西方價值」。生技科學則被官媒塑造為與美國競爭的「國家英雄」。
彭博新聞指出,中國不僅對科學研究的限制寬鬆,還投入巨額政府資金。單是2023年,北京當局就在生技領域挹注約30億美元。中國的細胞與基因療法銷售額去年達3億美元,至2033年可望成長至20億美元。
如今,中國對大型動物的基因改造研究頻頻登上國際媒體,種類之多、實驗規模之大令人震驚。中國科學家培育出有思覺失調(精神分裂)、自閉與睡眠障礙的猴子;率先成功複製靈長類動物;製造出罹患代謝與神經疾病的基因改造犬;甚至成功複製具有凝血功能異常的基因改造米格魯犬。
中國智研諮詢公司估計,2024年,全球生技研究中的基因改造動物市場規模達150億美元,較10年前成長一倍。在此之前,相關動物的銷售由美國企業主導,大多是販售植入人類疾病基因的小型哺乳類動物;但中國以政府資金挹注這類大型研究中心,已急起直追。
這樣的發展趨勢引發安全與依賴風險。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(Merics)指出,中國的生技產業快速崛起,可能使美歐的醫藥供應鏈在地緣政治競爭下出現弱項。
此外,基因編輯屬軍民兩用技術,不僅可用於醫療,也可能被武器化,甚至可能發展出生化武器與基因改造的病毒。墨卡托中心學者雨龍(Jeroen Groenewegen-Lau)指出,歐洲若缺乏相應能力,可能來不及反應。
報導稱,中國是全球實驗用動物的主要供應國之一,自2010年以來興建了八座國家級動物研究中心,涵蓋小鼠、兔子、鳥類、犬類、靈長類,研究用猴子的數量在全球名列前茅。
2019年,中國啟用兩間國家出資的基因研究中心,專門研發用於醫學研究的豬與靈長類動物模型。
法國波爾多大學神經退化疾病研究所創辦人貝札德(Erwan Bezard)直言,中國在繁殖基因改造動物方面,幾乎擁有「壓倒性」的能力。
貝札德表示,以常用於藥物與疫苗研發的獼猴為例,通常需要數十甚至上百隻雌猴進行繁殖,才能得到一隻活體幼猴,「這很明顯是一大挑戰,只有中國能做到」。
中國也是第一個複製靈長類動物的國家,複製猴「中中」和「華華」2018年成為國際學術期刊《細胞》的封面故事。
之後中國科學家又將複製與基因編輯結合,製造出許多有相同睡眠障礙、焦慮與憂鬱症狀的猴群,藉此更精準、更快速研發治療藥物。中國科學院院士蒲慕明2024年還表示,將利用靈長類動物實驗模型在五年內研發腦部疾病藥物。
但批評者認為,大型動物太接近於人類。專研生物倫理學的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社會醫學學者沃克(Rebecca Walker)就表示,體型較大的動物是否比體型較小的動物具有更高的道德地位,成為學界爭論焦點。
牛津大學遺傳學家與生殖生物學家葛林菲德(Andy Greenfield)則指出:「許多大型動物是群居動物,有感知能力,能感受到快樂和痛苦。」他認為,這類動物實驗「必須經過非常仔細的論證,確認能帶來實質好處,不能只是出於好奇心而進行的研究」。
回到賈怡昌的漸凍症療法研究。那頭小豬腳步蹣跚的畫面,仍鮮活存在他的腦海中。
漸凍症盛行率極低,全球每十萬人中僅有二至六人罹患,因此研究經費稀少。不過,每一年仍有成千上萬患者逐漸走向死亡。物理學家霍金(Stephen Hawking)、被譽為美國職棒大聯盟最偉大一壘手的盧蓋瑞格(Lou Gehrig)都曾讓世人清楚看見漸凍症的殘酷:先是肌肉無力,接著癱瘓,最後呼吸衰竭。
賈怡昌說,雖然每次解剖動物都令他心懷愧疚,但他仍認為,要發現疾病的運作機轉及研發藥物,建立動物模型仍然不可或缺。
葛林菲德則指出,即使賈怡昌參與研究的漸凍症療法真能成功,動物實驗的倫理爭議也不會因此結束,「我們一定要問:研究是否真能帶來表面宣稱的利益?如果答案是肯定的,那要如何在造成最少痛苦的前提下進行,並使用最少的動物?」
最新more>
- 王金平新春宴 柯志恩、陳其邁、賴瑞隆出席!留下難得合影
- 初三出遊傳憾事!一家5口鯉魚潭遊湖翻覆 8歲男童受困不幸溺斃
- 大阪市獲捐21公斤金塊 指定用於更新老舊自來水管線
- 馬尼拉華人區驚傳分屍案 凶嫌落網自稱台灣籍
- 生日當天被捕!英前王子安德魯牽扯淫魔檔案 涉公職人員行為不當
- 苗栗發福袋 賴清德打趣:「請把我當財神爺」不分黨派幫助各縣市發展
- 韓股新春開門紅首破5600點 創業板指數漲太兇啟動Sidecar臨時停牌
- 「台灣滷肉飯有香菇嗎?」張鈞甯春晚後台突被問 一度遲疑引發熱議
- 北捷地圖不是北朝上!德國在台協會「好困惑」 網揭背後貼心設計
- 卸任小英去哪裡?山上都是她的「毛朋友」 拔菜也講求快、狠、準
熱門more>
- 高市早苗發表春節賀詞 刪除「華僑華人」引解讀
- 谷愛凌在美生長卻代表中國出賽 美副總統范斯說話了
- 羅浮宮遭中國導遊詐騙十年損失3.7億 門票重覆使用、每天放行20個旅行團
- 分析:中國對非洲全境宣布零關稅政策 但想倚重的非洲同伴是哪種國家?
- 「今天,我為龍一滑冰!」七年羈絆逆轉勝 「璃龍組」為日本雙人花滑摘首金
- 中國威脅菲律賓「數百萬人恐失業」、譏議員「以為自己是誰」 菲外交部強烈異議
- 送宜蘭超大紅包 !卓榮泰宣布:「宜蘭至羅東鐵路高架化計劃」行政院已同意
- 8台星登央視春晚合唱〈寶島戀歌〉、他牽花蓮小女孩上台!伊能靜喊:中國台灣會感動
- 2026最受矚目「漫改真人版」要來了!《我獨自升級》、《驀然回首》、《海洋奇緣》期待值爆表
- 曾因川普削資幾乎停運 自由亞洲電台恢復對中國廣播

